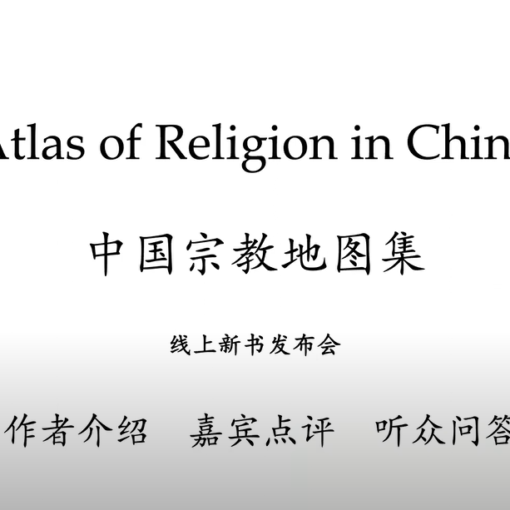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行动的解析 ——一个后现代观点
2019-01-02 谭光鼎 陈鸾凤
本论文之目的是解析基督徒聚会处的教会治理模式,并探讨它们对西方基督教支配权力的挑战与抗衡。基督徒聚会处具有独特的教会治理观点,包括长老职责、事务处理、圣徒事奉。这种治理模式源自于圣经教义,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治理必须顺从圣灵运行,因为基督是教会治理权威的唯一基础。基督徒聚会处批评教会宗派与差会,因为它们垄断所有教会的治理,限制并取代长老和所有信徒的角色功能。这种变相的事奉系统沦为一种科层组织,物化与异化的结果,扼杀了最基本的灵性功能。透过对公会宗派去中心化的诉求,基督徒聚会处否定宗教系统的支配权力;透过解构公会的霸权,它们恢复教会的独立自主;透过对差会权威去正当化的诉求,它们鼓励所有信徒参与服事,建立团体的事奉体系。综合而言,基督徒聚会处是一种后现代式的革新行动。透过它在本土化行动中的努力与成就,它们成功推动了基督教的改革。
关键词:基督徒聚会处、教会治理、本土化、后现代主义
壹、前言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可考者已逾千年。十九世纪之初,更正教会开始进入中国大陆,不仅在沿海地区,并且深入内陆各省,建立许多教会(教堂)。但无论传统的天主教会或新来的更正教会,究其根源,在教会设立、福音传扬和信徒牧养上,这些教会都有强大西方差会总会的支持与资源供应。因此,在民族主义意识逐渐升高之后,中国也兴起另一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趋势——本土化教会,希冀能脱离来自西方之宗教力量的支配,使基督教在中国产生独立自主能力,或者说,使基督教更贴近于圣经所启示的路线。
二十世纪初,在宗教殖民势力与基督教本土化的交错激荡之中,一些本土传道人,受到圣经教义的启发,投身于教会开展和圣经思想的研究之中,并且积极出版各种刊物,传播圣经启示教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自一九二〇年代起,基督徒聚会处于中国各城市中逐渐开始设立,并借着信徒移民的脚踪,朝向东南亚国家发展。在教会的性质上,基督徒聚会处属于一种中国的自立教会型态,以实际行动具体实践“自立、自养、自传”的牧会方式,独立运作,同时也诉求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之殖民霸权的抗拒。
教会的性质迥异于一般商业机构,不以营利为诉求,而以传福音和教导圣经真理为目的,因此属于一种“非营利的、以人为导向”的服务型社会组织。对于任何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机构而言,组织管理是提高绩效的重要手段,无论资源的控管运用、组织结构的设计、人员权责的分配、领导与评鉴机制的运作等,都讲究管理的观念与技术,以促使组织充分发展,并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对于这些自立教会而言,既无来自西方差会的后勤资源,亦无形式化的层级组织架构,却能够以一种自给自足的方式运作自如,并且迅速在各地扩展。
相较于传统西方所建制的基督教系统,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督徒聚会处,其组织特质为何?这种以小众为对象的服务型组织,如何进行其内部管理?这种以地方为界限的社会组织,其运作机制为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虽然此种自立教会之领导者的圣经思想广受一般基督徒的欢迎,但是对于它们独立运作的观点方面,在基督教团体中也有一些矛盾的看法(李佳福,2001;姚西伊,2005;蔡谨图,2005;邢福增,2003;彭淑卿,2010;邓世安,2009)。因此,究竟教会的治理方式是否应该完全摒斥组织体系,脱离跨区域组织,淡化各种人治色彩的管理制度?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职是之故,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基督徒聚会处的组织管理和特色,以及它们对于西方宗派和差会制度的批判。作者尝试梳理基督徒聚会处对于教会型态的基本论述,分析其事奉分工与运作的原则,并运用M. Weber 之科层体制与权威类型,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观点,进行一些综合讨论,借以分析基督徒聚会处的主要特色及其本土化成就。
贰、教会治理的模式
一、教会的基本型态
关于教会之治理的模式,无论长老的职权或执事的处理事务,其最重要的乃是教会的基础究竟如何。教会的基础是一个“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决定了其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教会的事务)的实际运作。所以在独立自主的教会里,其管理模式就和公会支配系统的教会有所不同。
依据圣经的内涵,教会的型态有两方面,宏观的(macro)与微观的(micro)。前者系指所有信徒的集合,不分时间,不分地方,这是一种完美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是长久且普遍存在的教会典型。后者系指在时间与空间的脉络里,于一时一地所出现的各个教会,是多数的、分布于各地的,如同圣经中所说的“各教会”(徒九31)、“七个教会”(启一4)、“众教会”(林前十一16、十四34)等名称。
在微观的教会型态方面,教会都是她所在的地点(城市)为名称,诸如哥林多、以弗所、耶路撒冷、安提阿、腓立比等教会;在权责的运作方面,并没有跨越几个地区之间的联合教会,也没有超越各教会之上的大型组织系统(倪柝声,1979,pp.117-150)。
微观的教会型态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为了维持教会共同的见证,她们之间也需要维持一致的、共同的行动,彼此扶持,尽力周济,相互效法学习。此外,每个教会也应当学习受圣灵引导,接受使徒的教导(林前四17)、遵守神的命令(林前七17)。虽然居住地区的分隔使教会分为许许多多单位,但是各个教会之间,应该有灵性的交通,以保守她们在见证上的合一(倪柝声,2002e,p.128)。
二、教会的组织分工
依据结构功能理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观点,个体的组织行为基本上决定于组织“结构”因素。“结构”系指组织中的角色结构,角色结构决定了“组织人”(organizers)的分工,也建构了个体的行为模式(角色规范)。而实际的角色行为是否符合角色规范,将影响组织功能的发挥(Parsons, 1966, 1971)。
教会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组织,就其特殊的性质而言,她的组织分工分为“造就”和“管理”两方面。前者属于灵性工作,类似教育训练,较偏重在宏观一面的功能;后者属于物质工作,是组织内部的行政管理,偏重微观一面的功能(详参表1)(倪柝声,1979,pp.130-40, 11-113;2002a,pp.124-133;2002b,pp.214-216)。
在“造就”方面,主要包括“使徒、先知、牧人、教师”(弗四11)。这些人物都有某一种“圣灵所赐的恩赐”,或是从神的恩典而获得的“才干与能力”。他们受神差派,出外到各地教会为神作工,包括传福音、设立长老与执事,或是讲解教导圣经真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弗四12)。由于历世历代以来这些重要人物不断发挥他们的角色功能,所以神的教会才能得到建立和扩展。
在“管理”方面,主要人物是指教会里的长老和执事,前者肩负带领和监督职责,后者办理一般庶务工作。基本上,这些人都有从神而得的才干和能力,但他们的是属于教会微观的一面,职权不跨越一地一会。他们除了负责教会日常的事务管理之外,长老们也必须担负一些灵性教育的工作,“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前五2)。
表1 教会事奉的组织分工
|
宏观的教会
|
微观的教会
|
|
|
分工角色
|
使徒、先知、牧人、教师
|
长老、执事
|
|
权威来源
|
神所立的
|
人所立的
|
|
角色功能
|
造就
|
管理
|
|
行为模式
|
出外至各地为神作工(传福音、设立教会与长老、牧养教导信徒)
|
在当地管理教会(监督、管理、牧养、庶务)
|
|
工作性质
|
灵性工作
|
物质工作
|
数据源:倪柝声,2002a,pp.124-125。
三、教会中的长老治会
依照圣经所揭示的,在个别教会的行政管理中只有两种人:长老、执事。而这二种人中,长老的职责最重,也是最主要的角色。依据圣经的记载,长老的角色基本上具有四种特质(倪柝声,1978,pp.5-9, 170;1979,pp.104-114;2002a,p.128)。
首先,长老是“由圣灵所设立”。长老的产生,内在是根据圣灵的印证(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外在是由使徒所设立(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徒十四23)。从新约圣经来看,长老的设立并非根据使徒之个人的喜好,也非来自当地信徒们的选举。圣经从未记载任何一个教会有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选举他们的长老。所有的长老都是“神所已经设立的”,使徒乃是设立“圣灵所已经设立的”,因为一切在教会里的事务都应当以圣灵作主,所以先是圣灵有所显明,使徒再依照圣灵引导,祷告印证圣灵所立的人为长老。
第二,作长老的人必须有属灵根基,他必须是一个认识属灵事情的人。由于教会是一个从事属灵活动的社会组织,所以担任长老的人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也是一个有属灵知识,在属灵上有价值的人。作长老的人虽然也需要具备才干,但设立长老时,必须以属灵根基为基础,再斟酌他的才干与能力,绝不能只看外表的成就、历练、名望和地位。这样,长老才能在牧养圣徒和治理教会上作出正确的带领,正确地引导圣徒方向。
第三,长老的职权仅限于他所属的教会,他既不能跨越地区的界限,也没有超越众教会之上的长老。虽然教会和长老是由使徒所设立,使徒也有牧养众教会的功能,但是一个教会的治理和领导,其权威都在长老手里,并不在使徒手里。这样一来,才能保证教会在行政上完全独立,维护“就地为政”的性质;并且也才能避免各种宗派体系之跨地区的支配,造成了宏观教会的分割与区隔。
第四,长老对于教会的管理,是一种“多数人治理”的模式,而非单一领导或寡头领导。从新约圣经记载来看,各地教会的长老(或监督)都是多数的,例如“众长老”(徒十一30、提前四14)、“长老们”(原文多数)(徒十五2, 4, 6, 22、十六4、二十17、二一18、提前五17、雅五14)、“诸位监督”(腓一1)等。虽然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制度都采取“单一领导”方式,但是圣经中从未记载单一领导的模式,也从未有一个人负责全教会事务的事例。因此,由欧美传教士所建立的教会管理模式(一人治会制),虽然事权集中,运作轻省便利,但这种管理方式并不合乎圣经。尤其,在缺少权力的平衡下,“一人治会制”容易使教会被一个刚强的人格所支配,偏向寡头垄断或独裁权威,沦为个人的产业,或使组织文化呈现个人色彩。反之,“多数人治理”可以维持一种组织的动力(organizational dynamics),平衡各人的权力,使圣灵在领导中成为唯一的权威和基础。
四、教会中的全体事奉
教会的治理虽然是以长老为监督,以执事负责处理庶务工作。但在教会众多的事务与活动(服事、教导、劝勉、分授、带领、怜悯人)之中,并非长老和执事所能全部包办。依据圣经的启示,每一位圣徒都有主所给的恩赐(能力),使他们能在教会组织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发挥他们个别的功用。而那些特别有恩赐的人(使徒、先知、教师),其功能之一就是去教导并训练所有信徒,使他们都能产生功能。一个功能正常的教会生活,应当是个个参与事奉,人人尽其才能。
从新约所启示的教训来看(罗十二4-5、林前十二12),教会被比喻为一个生机体(organism),是一个活的身体,每一个信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因此也都是活的,是有功能的。如果身体之众肢体都具有生机功能,则教会中的每一位信徒也都应该赋有功能,也应当发挥其功能。只有每一个肢体都产生功用时,才是教会组织正常的状态。在旧约时期,只有祭司和利未人被安排来事奉神;但在新约时代,每一位信徒都是事奉神的祭司,他们被称作“君尊的祭司体系”(royal priesthood)(彼前二9),是一种“团体的事奉”,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事奉体系中都有他的角色和功能。
依照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和路加福音十九章的比喻,教会不是只有能干的人(五千银子、二千银子)在服事,那些能力最微小的人(一千银子)的人也有服事的功能。所以,治理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使每一个微小的信徒(一千银子)都发挥他的角色功能。既是基督身体的肢体,就一定有他特定的角色功能,他就该出来参与各种事奉。然而,我们若观察各基督教团体的实际状况,理想和实践之间仍有相当明显的差距。神职人员或牧师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事奉,无法使每一位信徒在这个生机组织中发挥他们的角色功能。这些形式化的事奉体制系已经成为一种居间制度,抑制了所有个别功能的发挥。
因此,教会治理的改革,教会行政的独立自主,其主要诉求之一,应是促使教会组织更为活化或生机化,促使有一千银子的人都有机会事奉。一个教会若是要能代表“基督的身体”,其充分且必要条件就是人人都作祭司事奉神;要成功的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就必须建立团体且普遍的祭司体系(倪柝声,1978,pp.61-79)
五、顺服圣灵权柄
社会组织的管理包括各种行政历程,诸如计划、沟通、评鉴考核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由于教会的性质较为特殊,在领导权力的运作、如何作决定、领导者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等方面,都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
依据圣经启示,在教会的治理中,最高的权柄是神,神自己就是权柄。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国度(圣别的国度——彼前二9),教会也被比喻为“祂的身体”(弗一23)。因此,神是元首,身体必须顺服元首的指挥。在教会生活里,神所设立的长老,或是其他有重要功用的人(使徒、先知、教师),乃是神权柄的间接代表。所有信徒不仅需要顺从直接的权柄(圣灵),也需要顺服那些间接的权柄。教会生活就是一种顺服神之权柄的团体生活。但是这种顺服,基本上是来自于信徒之间“神圣生命”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因此,教会本土化的行动目标之一,就是对抗宗教系统内的权力结构,突破人治色彩的层级支配,使教会回归“神治”。
在教会聚会所的本土化行动中,他们也着重将“神的权柄”具体实践于教会治理之中。例如在“长老议事”的过程里,“顺从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一项最高的原则。虽然在一般组织管理中,领导有许多种型态,包括民主、专制、权变等,不一而足,但在教会中,神是最高权威,所有的领导和议事,都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并且凭灵作决断。在长老的会议中,参与者可以自由发言或辩论,但在关键性的作决定(decision making)时,长老乃是让圣灵有主权,顺从圣灵引导而作出结论。因此,属灵领袖(长老)的决定,就是圣灵的决定。此外,在一般庶务的处理上,也必须让圣灵有主权地位,接受圣灵的引导。处理事务虽然需要运用许多属世知识和技能,但若只是挑选有干才却没有属灵价值的人担任执事,就容易把世界的手腕、办法、本领、聪明,都带到教会里来。即使事情办得顺利,但结果却可能降低教会属灵水平,使教会世俗化,与一般社会组织无异。
简言之,教会治理的方法,不是独裁专制,不是委员制,也不是民主制。教会的治理不是交由投票或少数人决定,也不是只凭借人的专业能力。乃是长老和执事学习顺从圣灵权柄,并且从圣灵得到智慧和能力。因此教会治理不是属人的、世俗的,而是属灵的、属神的,让神的权柄经过每一件事(倪柝声,1978,pp.123-124, 176-185;2002f,pp.186-200;2002g,pp.167-169)。
叁、对于居间制度问题的检讨
基督徒聚会处与许多同时代之独立自主教会的本土化改革,主要的背景脉络是长久以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在诸多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的冲突下,本土化的改革行动,不仅能解决教会治理的矛盾问题,也能使教会治理回归圣经的基本教义。
虽然圣经揭示出,教会是属神的,是由神的生命所构成。但以历史事实来看,二千年来的教会发展,由于人之意念和各种文化的影响,教会的实行不断发生各种偏差的路线。十五世纪宗教改革以后,虽然神兴起了一些特别有功用的人,诸如马丁路德(M. Luther)、卡尔文(J. Calvin)、韦斯利(J. Wesley),他们推动教会的改革,或在各地兴起神的福音工作。但是这些改革的教会或福音工作,后来逐渐形成各个宗派(denominations),依照他们的工作在各地设立教会,并且以跨区域、组织系统的方式支配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初,虽然有神的祝福,但后续发展结果,却使教会走向形式化,产生支配体系和权力层级,以致领袖、阶级、地位、教训、文化和种族因素,一一掺杂混淆了教会应有的面貌与实际(倪柝声,2002b, p.34;2002c,pp.59-62;2002e, p.132)。
从教会聚会处对于教会治理的综合论述中,各种角色分工划分得非常清楚,并不重迭,也不交互含摄。在宏观的一面,神把作工的职责交托给使徒和先知,他们可以照着圣灵的带领,运用每个人的才干能力去“造就”教会,使各地信徒成长。但并神没有把管理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们,所以他们不能越权干涉教会的行政,发展一种“居间的制度”(牧师、神甫),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或“代理者”。教会聚会处批评今天各基督教公会的制度化作法,其原因就是如此。这些“中间人”被雇用来管理教会事务,成为教会事务的代办者,不仅取代长老、执事的职责,也取代了信徒和神之间直接的交通。
虽然“使徒”在神的工作中是最大的恩赐,“先知、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也都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在微观的一面(各地的众教会),他们是没有地位、没有职权的,因为“管理”的职责是交托给长老和执事们。所以,“牧师”的任务不是去管理教会,“先知、传福音者”的角色也都不该长久局限在单一教会里。
今天关于教会的建立、圣徒的牧养、真理的陈明,确实需要这些有恩赐的人去发挥宏观的功用。但是他们不应当转化成为一种“制度”,成为包办事务的体制,代办所有例行性的教会事务;也不当发展成为一个“系统”,具有指挥中心和高低层级,超越各个地区、国家之上,调度人员与资源。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转化,产生三种不当的结果:限缩有恩赐者应发挥的功能、越权取代长老与执事的角色、剥夺全体信徒尽其功能的机会。
教会聚会处强调,虽然各种恩赐都是圣灵所赐给的,但是这些人的工作一旦形成制度,就必然限制了圣灵的自由,抛弃圣灵权柄应有的支配地位,使原有的“神治”偏离到“人治”,使人的企图和野心得到机会,渗透到教会的治理之中,使教会产生各种问题。不仅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僵化与疏离,使教会丧失其应有的生机功能。进而也可能产生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的问题,使神的教会产生分裂。因为教训、文化、语言、种族、国籍等种种差异,造成相互隔离与分割,破坏教会的整体结构。在教会二千年的历史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倪柝声,1979,pp.58-59, 140-147, 173-189, 297-304)。
肆、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意义的综合讨论
本文前述以五个重点——教会的基本型态、组织分工、长老治会、全体事奉、圣灵权柄——作为架构,勾勒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改革行动的的基本内涵。事实上,基督徒聚会处的组织管理及其运作,可以从两方面看出它的意义。若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她促使基督教的开展回归圣经基本教义,但是她也呈现一种基督教在中国之“抵殖民”(de-colonialization)的行动;若从基督宗教的支配结构来看,基督徒聚会处的主要诉求是解构(de-construct)西方宗派差会的霸权,而拒绝居间制度则是推动基督教本土化的主要行动策略。综以言之,在基督徒聚会处的教会治理模式中,他们尝试把教会从“人治”恢复到“神治”,从“科层化”回转到“生机化”,从“殖民化”扭转到“本土化”。
为了更深入了解基督徒聚会处之本土化行动的意义与价值,本文以下分别从支配结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含解构理论、后殖民主义)等三个角度,进行一些综合讨论与批判。
一、恢复神治的支配结构
在论到当代社会组织体系时,社会学者M. Weber依据历史发展事实,提出他独特的组织观点。他认为任何组织皆有它的权威(authority)依据,这些权威赋予组织和领导者“合法”基础,或称为“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Weber 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都有它的合法性,其中包括了命令(支配)和服从(被支配)两方面,二者的行为结构乃是建立于支配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合法的权威来自三种事物:习俗惯例、个人魅力(charisma)、法制规章。依据这三种基础,权威具有三种类型: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法理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陈介玄、翟本瑞、张维安,1989;Weber, 1947)。
这三种权威类型及其统治权力具有不同的特性。在传统权威方面,由于某些“习惯和传统信仰”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君主制度),权威乃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权力的递换一概依循传统制度。在魅力权威方面,权威是建立在某一个“特殊且具有魅力的人格特质”上,领袖人物运用其非凡的气质吸引群众,并行使他的统治权。在现代化社会里,法治是一切权威的基础,法治的基础使领导者获得正当性,因此正当的领导权力必须根据正式的法令规章。在现代社会中,法理权威居于主导地位。
在解析各种恩赐的组织分工时,基督徒聚会处根据圣经教义,把教会模拟为一个生机体,是一种有生命的组织。他强调教会有两方面的表显: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在宏观一面的教会,“神的家”乃是微观一面的教会。事实上,神的家也就是基督身体在各地方的代表或具体的显出。因此,神的家就是一种生机的组织,一种有生命的结构体。但无论是基督的身体或神的家,教会的领导、治理或事务处理,都应该跟随圣灵的引导,而不应该倚靠制度化的人事安排或公式化的办事方法。
基督徒聚会处格外强调,教会乃是“神的权柄”和“信徒顺服”的最高表现,在这个组织结构里,基督是元首,是最高的、唯一的权威,因此圣灵具有绝对的主权(宋志蒋,2004)。基于神的救恩,所有蒙恩的信徒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在教会中彼此服事,相互学习。教会中的领导者(长老/监督),他们的设立虽然直接来自使徒,但真正的设立者乃是神,使徒不过是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引导或印证,顺着圣灵的意思而行事。
所以在基督徒聚会处中,权威的基础不是“传统”,所有的服事者不是经由世袭或传统惯例而来,长老议事或执事处理事务,也都不倚赖习俗或常例,他们乃是在灵里接受神的引导而断案,或是从圣灵得到料理事务的智能。其次,教会的权威基础也不是“魅力”,因为长老和执事的设立,绝不是因为他们有属世能力、干才和技巧,乃是因为他们敬畏神,在神面前有学习,肯顺从圣灵。再者,教会的权威基础更不是“法治规范”,虽然教会行事必须遵守国家法令,但长老监督和执事办事的先决条件,乃是他们先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是跟从圣灵的人,受神管治的人。所以神在他们身上先有主权,先有支配,然后他们才能牧养群羊,办理事务。
除此之外,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们纵使能说预言,能带领许多人信主归神,能牧养许多信徒,但这些恩赐都不应该是一种“魅力”,吸引人来跟从他们。因为这些恩赐的源头乃是圣灵,并非属于个人的特质;恩赐运用的结果,也非为着建立自己的支配领域,乃是为着建造神的教会。无论他们在当地服事,或出去到各地尽职,也都不应该仅仅是依照习俗和惯例,而应该是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托付,接受神的差遣。在神的教会里,长老尽职不是一种萧规曹随、循例办事的消极态度,也不是标准作业程序去导引执事们办事,更不是在造就过程中发挥个人魅力的影响,成就自己的支配结构或统治王国。
职是之故,在基督徒聚会处里,长老和执事的权威基础,应该是神的权柄,是圣灵的运行,是基督的元首地位。教会的权威类型,应当称作“神圣权威”(Holy authority)。无论基督的身体或是神的家,教会应当是“神治”,而非“人治”;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治理,而非按照人的意念来领导。虽然在近代基督教历史上,不乏许多有魅力的人,受圣灵感动而牺牲奉献自己,到世界各处为主作工,传布真理,建立教会。但是经年累月之后,这些原本有灵性根源的服事体系,却一一形成各种不同的支配系统,建立各种系统化的制度。这样的结果就使基督的身体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分割隔阂。
二、拆解科层式的居间制度
M. Weber 在说明三种权威类型时,指出在法理权威的基础上,西方的理性主义发展出一种最具有效率的组织型态——科层体制(bureaucracy)。科层体制的产生,主要是为了因应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之需求,促使社会组织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对于组织人事、权责和资源,进行客观、有效的管理(Weber, 1946)。这种强调理性的组织型态虽然具有效率高、正确、迅速、客观的优点,但它的运作机制也被讥评为注重形式、刻板僵化、缺少弹性、繁文缛节。所以,Weber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58)一书的最后,也感叹这种最有效率的组织将发展成为人类的“钢铁牢笼”(iron cage)。
不仅如此,1930 年代后兴起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或称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也对这种出自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产物提出强烈批判。批判理论强调,原来推动启蒙运动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逐渐发展出以“技术——目的”为导向的现代文明,但这个理性的发展却也产生吊诡的反转,因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庞大技术操控力量,扼杀了原来的实质理性,使现代文明沦为一种科技政体(technocracy),当它在建立理性化的社会秩序时,同时也宰制个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个人自由与自律。当一切社会生活都走向条理化、工具化、科层化后,价值的澄清、辩证的思考、伦理的判断,都将沦丧殆尽(高宣扬,1995;Adorno & Horkheimer, 1972; Eisen, 1978; Marcuse, 1964)。
在厘清各种恩赐的组织分工时,基督徒聚会处提出“祭司体系、全体事奉”观点,并对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组织发展,屡屡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起初时,许多有恩赐的人确曾被主兴起,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一旦建立制度化的运作机制——差会——之后,神职人员(牧师、神甫)就成为一种“居间制度”,取代所有信徒应该发挥的功能。“一人治会”或“代理制度”虽可能是有效率的作法,把属灵的、事务的工作都包办在一个人身上,但这样的作法却不合圣经的启示。“差会体制”虽然可以进行跨国式的调度,有效地控管人力物力资源,但这种运作机制扼杀了基督身体上所有肢体生机的功能。
那些最初建立宗派的属灵伟人,他们所凭借的属灵力量,无疑地是一种实质理性。他们之所以能为神牺牲奉献,是因为他们依循一个伦理的判断,实践一种价值的抉择,采取一种自律自发的行动。但是一旦宗教活动形成了一个支配结构(职务层级),一旦教会管理建构出一种组织体系(总会/支会),一旦教会事奉发展成一个层级系统(牧师/平信徒),基督宗教的科层体制就隐然成形。这个科层体制之物化(reification)与异化(alienation)的结果,反而使差会体制成为一种霸权,凌驾个体之上,消解了个人从神所得的启示与呼召,扼制圣灵的运行。甚至这种宗教事奉系统的运作机制,无论是巨观的差会体制,或是微观的各地教会,都可能取代了神的权柄,成为替代的支配结构。这种体系虽然可以有效控管教会事务、调度人员资源、拓展教会疆域,但是制度规范取代了神的主权,例行公事取代了圣灵运行,技术效率取代了生机活力。简言之,以神作权柄的教会治理,因为科层化的系统,失去祂的同在与恩典;以人为导向的教会事奉,因为形式化的制度,刻板僵化而缺少生命。
面对西方基督教多年来在中国的拓展,基督徒聚会处认为,圣经中没有罗马总会,只有就地为政;圣经中没有宗派主脑,只有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有恩赐的人);圣经中没有跨国际的宗派体系,只有基督的身体;圣经中没有一人治会,只有圣别的祭司体系(全体事奉)。只有依照圣经所记载的事例,实践以地区为限的教会治理,才能脱离宗派体系;只有在城的范围内就地为政,彼此交通帮补,才能建造基督身体。把教会治理限制在地方范围,才能脱离宗教的科层体制;把教会治理的权责回归给长老执事,才能实践属灵的实质理性;把教会的事奉还原给所有信徒,才能真正建立神的教会。
综以言之,基督徒聚会处所推动的改革行动,基本上就是一种基督教本土化运动。对他们而言,基督教的本土化实践,就是在独立自主中落实教会的治理与组织管理。而这个本土化实践,恰恰也就是实践圣经真理的最正确之道。
三、解构公会的宗教霸权
基督徒聚会处和他们同一时代的其他本土化改革运动,都带有一种浓烈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色彩,对于东、西方的基督教界而言,无可讳言是一个激进的挑战,挑战长久存在之宗派与差会体系的正当性(legitimacy)。尤其对主要由西教士所建立之中国的基督教,他们强烈质疑并批判这些会堂、宗派的正当性。他们的观点也属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因为在近代史进程中,基督宗教从西方向东方传播,基本上是依附着西方国家殖民势力的延伸。所以从后殖民主义而言,基督教各宗各派共同建构了一个基督教国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而各种差派制度和牧会事奉,更使这个文化霸权得以深化。
基本上,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主要是批判现代主义之对于普遍性、共通性、绝对性、规范性、统一性的诉求。但是后现代也包含创新的力量,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的自我突破的创造精神,探索多元的创新道路。透过对于主体、自由与解放的诉求,后现代主义怀疑结构的先验性、固定性与确定性,在批判反省之中消解对于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上的统一性,从而发展出一种去中心化、去正当化、多元化的态度。尤其是在传统的巨型论述(grand narratives) 中,各种话语和论说的“意义”与“逻辑”,都隐藏着权力的运作。统治权力的支配产生各种巨型的知识论述,以致真理的真伪,道德的判断,都依附于权力关系(Foucault, 1980)。在统治权力支配下,社会与文化中隐藏着“主体/客体”、“中心/边陲”二元对立模式,而这种结构就是使传统社会与文化秩序得以“正当化”的基础。因此,解构的目的之一,就是颠覆这个正当化根基,批判并揭露道德论和知识论之背后的权力运作奥秘,进而超越而重建社会文化(高宣扬,1999;杨大春,1994)。
依照后现代的观点,传统基督教庞大的宗派系统和差会制度,已然形成一种“系统的、同一的、先验的、规范式的”结构。在“中心——边缘”的权力支配关系里,他们的知识论、道德论、正义论,都和权力相互共生,形成“权力——知识”的共生结构,这个共生结构就成为“正当性”基础。而宗派、差会的所有指挥调度,教会中所有事奉层级的运作机制,都在这个正当性基础上获得权威,行使权力。但是当宗派体系和差会制度物化并异化之后,这些原具有属灵意义与功用的运作机制和它们背后的理论基础,就都反转成为宰制的结构体,抑制个体的灵性,消解个体应有的属灵功能。整个教会体系的运作,不过就是一个缺少灵性与生机的结构体,其中角色错置,功能不彰,并且充满人治色彩(各教派特色)。
职是之故,当基督徒聚会处提倡回归圣经而实行教会生活时,他们的论述对于传统基督教而言,即是一种解构与超越的力量。他们一方面挑战并批判宗派与差会制度,另一面则尝试从边缘地位开启多元观点,使僵化而缺少生机的基督教,回归到最素朴的实行;使阶层化的事奉结构,回归到平等、普遍的祭司体系。
综以言之,基督徒聚会处的本土化改革行动,对于传统基督宗教而言,产生以下三种革命性的行动,挑战并颠覆基督教公会的统治霸权。
第一种行动是使教会“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去除以任何地点、道理、教训、人物为中心的巨型教会体系,拆解以西方政经文化为背景的宗教组织结构,打破差会宗派得以运作的中心权威。因为这些系统化、制度化的宗教组织,不但背离了圣经基本教义,更在层级体系之中建构出种种权力结构(尼哥拉党),使教会成为宰制个体的组织。透过“边缘”的发声与行动,使原本受“总部”或“总会”支配的各地教会,从“自主行政”的实践中找回她们的生命力,从“长老治会”中重建她们的主体性,从“跟随圣灵”中恢复基督的元首地位。
第二种行动是反基要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颠覆传统基督教对于教会组织的论述与实行。基督徒聚会处所主张的教会治理模式,犹如一种解构行动,尝试从多元的、弹性的、对立的观点出发,颠覆并解除传统巨型论述的束缚,脱离那些建立了宗派与差会之正当基础的绝对普遍真理。换言之,他们所强调的“恩赐与职分”之分工,就是否定“居间制度”(牧师、神甫)的基要性与必要性;他们所实行的普遍祭司体系,就是拒斥巨型的普世教会体系,抗拒东西方教会之间阶层化的权力支配结构;他们的“自立自主”,就是一种对宗派差会之集权主义的最大挑战。
第三种行动是去正当化(de-legitimation)(高宣扬,1999,p.90),抛弃传统以宗派和差会制度为主的教会管理思维和作法,解除传统基督宗教之结构主义式的单一意义和束缚。当宗派和差会的本质与意义受到批判,它们的中心地位和权威基础被抛弃后,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行之多年的基督教系统运作和制度规范,就不再具有正当性,不再绝对确定,也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唯一真理。一旦教会的行政“地方为限、身体合一”时,教会的真理和意义就能够还原到最符合圣经的素朴(naive)状态;一旦教会的信徒“各尽其职、全体事奉”时,教会的组织管理就能从形式化的“人治”还原到生机式的“神治”;一旦教会的治理“圣灵作主、凭灵而行”时,各种恩赐与职分的配搭就能使基督元首权柄获得神圣的正当基础。
伍、结语
作为本土化的改革运动之一,基督徒聚会处的努力与实际行动,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里,不仅鲜明地扬起去殖民化旗帜,并且成功取得教会扩展的实际成效。他们对于“顺从圣灵、自立自主、全体事奉”之理想的追求,一方面是衬托出神真正的心意与目的,另一面则充分表达对宗派和差会之“去正当化、去中心化”诉求。
在西方基督教强大势力之下,基督徒聚会处和其他自立教会的努力,毋宁是出于一种革命的、颠覆的、前卫的思维。在他们所采撷的圣经依据和详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组崭新的观念和实践,不仅挑战既有的宗教权力和制度,拒绝承认西方宗派和差会的无上权威与地位,他们更寻求一种超越,一种逆反,一种还原,也就是揭示一种更贴近初期教会历史的观点,使教会的组织管理更符合圣经真理。如果套用后现代主义的用字,“基督徒聚会处”无疑的是一种“后宗派”(post-denomination)行动,也是一种“对立霸权”(countered-hegemony)的建构。试图在抗拒宗派与差会之制度化权力之同时,提出一种更具真理基础且生机活泼的教会组织管理途径。不仅如此,在恢复教会治理的自律与自主之中,使各地教会得到培力(empowerment),得以脱离跨国事奉系统的霸权宰制。
然而,在这些本土化改革观点中,不免有一些仍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基本上,这些问题都集中在“合一——独立”上。例如,在脱离宗派体系或差会制度之后,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将会发展到何种情况?能否达到真正的“合一”?或是无可避免地走向独立、分立与孤立?换言之,在“自立自主”与“合一”之间,理念类型(ideal type)与实际表显之间,究竟是可以互证为真?或二者之间仍存在某些差距?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待更多的实践与检讨。虽然从教会历史的实例而言,众教会之间所产生的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Durkheim, 1984)似乎力有未逮,无法抗衡各种分裂出去的力量。但是在圣灵的主权的基础之上,各种改革行动也不断尝试突破种种障碍,追求如何在自立自主中,使教会维持合一的见证,如何跨越语言、文化、族群、国家的隔阂而产生合一。
这些问题都是关心教会见证的人,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奉献并投身于教会治理的人所该继续努力的方向。或许我们仍在等待历史的答案,或许期望神的权柄能胜过一切人治的影响,保守神的教会不受破坏。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六十余年来的教会发展中,或许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具体的例证,对于如何在“独立——合一”之关系中取得平衡,找出有更确证的答案与出路。
(参考文献)
李佳福(2001),《倪柝声与地方教会运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
宋志蒋(2004),《作为生命实践的理解与诠释:倪柝声的神学诠释学概要》,独者,5,115-138。
邢福增(2003),《倪柝声与三自革新运动》,《建道学刊》,20,129-175。
倪柝声(1978),《教会的事务》(台湾三版),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1979),《工作的再思》,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a),《通问汇刊(卷一)》(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五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b),《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一)》(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一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c),《特会、信息、及谈话记录(卷三)》(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十三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d),《初信造就(下册)》(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四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e),《复刊敞开的门、复刊复兴报(卷二)》(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f),《鼓岭训练记录(卷一)》(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三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倪柝声(2002g),《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卷二)》(台湾三版),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十三册。台北市:台湾福音书房。
林钟沂、林文斌译,O. E. Hughes 原著(2003),《公共管理新论》,新北市:韦伯文化。
姚西伊(2005),《书评:邢福增著〈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39,197-200。
高宣扬(1990),《解构主义》,台北市:远流。
高宣扬(1990),《新马克思主义导引(修订版)》,台北市:远流。
高宣扬(1999),《后现代论》,台北市:五南。
陈介玄、翟本瑞、张维安(1989),《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北市:巨流。
彭淑卿(2010),《成为基督荣耀的新妇:倪柝声的末世教会论初探》,独者,20,95-132。
杨大春(1994),《解构理论》,台北市:扬智。
蔡谨图(2004),《书评:邢福增著〈反帝‧爱国‧属灵人——倪柝声与基督徒聚会处研究〉》,《山道期刊》,8(2),203-207。
邓世安(2009),《倪柝声教会思想之研究(1925-1938):一个中西对话的面向》,《辅仁历史学报》,24,257-329。
Adorno, T. W. & Horkheimer, M. (197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Durkheim, 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Eisen, A. (1973). The meanings and confusions of Weberian ‘ration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9, 57-70.
Ellis, J.M.(1989). Against deconstru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Gerth, H. H. & Mills, C. W. (Eds.)(1991).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Marcuse, H. (1964).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ARK.
Parsons, T. (1966).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Parsons, 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Weber, M. (1946). Bureaucracy. In H. H. Gerth &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eber, M.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Weber, M.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