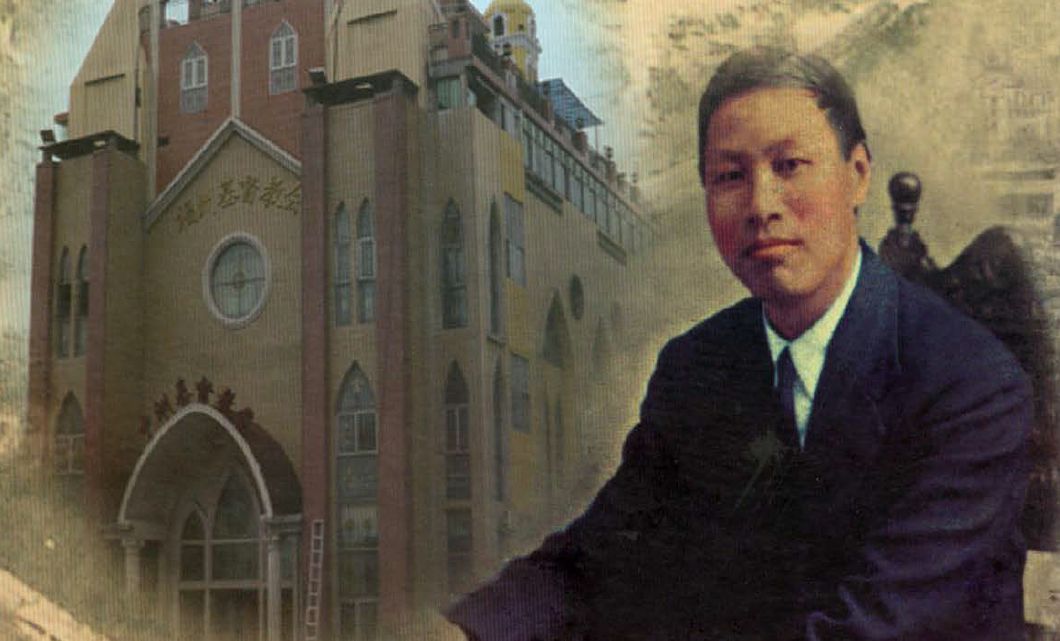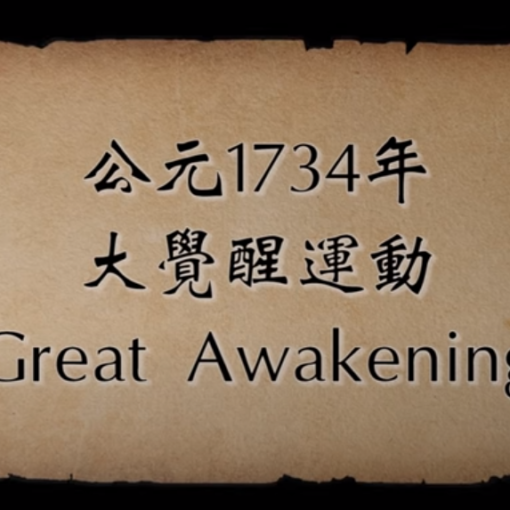原文链接: https://shengjingzhenli.com/m/articles/_id?id=724
4.3. 反思和警醒
在从启示录前三章中获得关于教会的预言和预表中,倪柝声对他所“看见教会的预言”做了一个总结。他确认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是预言,而且都在教会史中应验了。他的小结部分同样体现出他的谦卑和谨慎。他指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一件事,不管教会处在怎样的情形中,每个教会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人如果在神面前是忠心的,就要寻找出自己该怎么办。主给我们看见那个解决的方法。主说,祂就是道路,祂就是真理,祂也是生命(约14:6)。所以,不管在那封书信中,在任何情形下,主并不叫我们注意情形多糟,乃是叫我们看见他自己是谁。启示是恢复看见。”[103]
倪柝声不是在指导神学生写学位论文,也不是自己在做纯学术考证和论证,他是在查经,在牧养会众。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在最后要进入现实的中国教会。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也注意到了弟兄会传统的教会。他将之作为历史上依然存在并发展着的第四种类型的教会,即老底嘉教会所预表之教会。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地方教会,在他的时代,是力争回避宗派教会所有的组织机制的弊端或不足。他不愿意自己创建的使徒传统的教会有一天会变成宗派教会。“在这个时代中,神给我们看见有四个不同的教会。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罗马教、更正教、弟兄相爱和弟兄会。第四个的弟兄会,它已经落到老底嘉的地位上了。以那个团体说,已经变成一个宗派了。”[104]
应该确认,在倪柝声的属灵看见中,宗派教会不是他理想和远象中的中国教会。他强调弟兄之爱完全是主耶稣门徒之间所显现出来的爱,也是符合耶稣基督最后新命令之爱(约13:34-35)。
全部围绕着启示录中的七个教会所获得的预言、预表及历史性的启示以最后一句话,结束倪柝声的理解和分析。这句话可谓倪柝声教会论的基本理念或原则:“求神给我们走一条正直的路,无论如何,我们要拣选非拉铁非的路。”[105]
“一旦我们全然确认了七信息对七教会的特殊意义,就可以问:约翰的思想中有没有其他读者?为什么他写给七所教会?这七所教会总不会是亚细亚省内的全部教会,而约翰也一定期望他的著作可以从这七所教会传递给同区的其他教会,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看来,在约翰的思想中,他的预言是整个圣经先知传统的最终高峰,这背后的权威意味着启示录对所有基督教教会都是相干的,而这也必定是‘七’这数字所指向的意义。我们在本书将经常察看启示录中数字的象征意义。七是完全的数字,约翰写信给七所教会,显明他是写给代表所有教会的七所具体的教会。这个结论可以在七信息每段的重复句——呼吁读者留意预言的句子——得到证实:‘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2:7,11,17,29;3:6,13,22),看来是邀请所有读者一同聆听给七所教会的每一段信息。”[106]
非常关键的是,七个教会的预言结束时,倪柝声并未引入千禧年传统的终末论结论,也就是说,他讲老底嘉教会预表中的最后得胜者与宝座作为整个神所预言中的世界历史的最终极端。他的教会论在这个地方进入荣耀的基督这一异象,的确与非信经教会传统的终末论之灾变和失败论不一样。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需要就其全部著作给予探讨其究竟是怎样的思考和领会。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和思考一下德国归正宗神学家,也是享有公共神学界盛名的大思想家莫尔特曼的一段文字:
“在终末的盼望中,再也没有像基督和属他的于历史终结前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的理念那样吸引人,并同时带来那么多的灾难。‘预言家、苦思冥想者和狂热分子’强化了这个理想。人们为了‘千年国度’离开家园并且朝着它迁移。殉道者为了‘千年国度’受苦并牺牲性命。人们为了‘千年国度’被逼迫、驱逐和谋害。基督教的历史在许多方面等于‘千年国度的争战’(Norman Cohn)。这种期盼存在于那些尽可能远离世界的小教派,如安息日会、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这种理念也存在于向万民宣教的教会的差派意识中。它也存在于征服外族并成为世界强权的基督教帝国中。最后,它也存在于把‘千年国度’期待成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锡安复和的‘基督教复原主义’的形式中。宗教的、教会的和政治的弥赛亚主义产生于这个理念。因此,我们必须严肃看待这个理念,对它进行神学的思考,不要立即就将它逼到异端史的范围,或是将它列入大教会对千禧年主义的弃绝中。” [107]
同样深受时代论影响的倪柝声,为什么没有在七个教会的预言中,最后把终末的思考纳入其中,而是将“荣耀的基督”这一异象作为“荣耀的教会”之本质加以强调?显然需要我们从其神学思考的本质去思考和研究,而不是仅仅注意他从西方弟兄会传统那里获得什么益处和启发而照搬进当时的中国教会。
5. 使徒传统与中国本土教会:爱邻舍、爱祖国、爱人类,荣耀归主
在简单地介绍和评述了倪柝声特殊的教会论神学观之后,我们需要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倪柝声对启示录中的预言和预表所做的历史时代的确认与他所赞成的19世纪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运动,特别是达秘的时代论有非常特殊的亲缘性。值得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论证,看看时代论神学传统在华人基督教界拥有的影响中究竟包含一些怎样的历史的社会学的,乃至心理学的诸般因素。因为不仅仅是地方教会的史观、救赎观和终末观,连其它非信经教会传统的福音派独立教会,都持守大致的圣经观和神学观。
其次,我们还需要研究倪柝声所孜孜以求探讨与建立的“弟兄相爱”式教会,以何种组织机制来拓展事工的?因为无论是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信经传统的教会,还是以丁光训为代表的获得国家唯一合法权利的“三自组织”,都有一个完整的行政序列和构架,来培训、督察和监管牧师阶层或圣品阶层。而“地方教会”按照非拉铁非的预表,达秘等的19世纪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传统,也出现了才二十年事工就出现弟兄不和的分裂状态,这个历史事实,使得倪柝声在分享启示录七个教会预言时,专门将“弟兄们的运动”与“弟兄会”区别开来,特别赞赏的是“弟兄们的运动”,是“弟兄相爱”的非拉铁非教会;而“弟兄会”则是开始不是倒退到撒狄,就是骄傲、纷争、分党,最后分裂为老底嘉教会。
宗派主义造成的教会之间在世俗利益层面的纷争、分裂与冲突,在倪柝声时代已经非常明显,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西方基督教新教内部的一大看上去无法减缓的苦恼与困境。在学术领域的研究来看,新教教会整体上经过改教时期的世俗人文主义、十七世纪的以古典主义和唯理主义为旗号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十八世纪启蒙主义和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进化论等思潮,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神学造成了在世俗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西方基督教文明整体上开始衰微,尤其是基督教主流教会。将宗教信仰私人化,教会退出公共空间等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当成一种崇高的价值系统。[108]
这一矛盾和危机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同样地不可减缓和避免吗?倪柝声以“非拉铁非教会”之预言来提醒他那个时期自己所在的教会诸位弟兄姐妹,实在是具有历史性。幸亏他的观点被参与查经分享的会友记录下来,成为历史教会的珍贵文献,成为中国基督教神学观对世界基督教神学传统的美好见证。
莫尔特曼在战后的成名作《盼望神学:基督教终末论的基础与意涵》一书中有与倪柝声类似的思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换时空做历史视野中的琢磨与研究。他写道:“教会及其神学既不是这个或那个社会的宗教,也不是某个宗派。既不能要求它迎合社会中个别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对真实性的理解,也不能期待它将自身表达为某一排他性团体的专断性语汇。教会与它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处于真理的过程;同样,神学也有份于教会的使命。它必须与历史观及世界观处于真理的将来过程中,因此,它也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争辩。如果在此对现代史学真实性概念的折冲与争辩所涉及的是耶稣复活的谜一样的真实性,那么便绝对不是为了遥远过去的细节而争辩,而且获取历史确定性的史学方法也会因着这个真实性而遭受质疑。这是一场为了历史的将来、认识和盼望的方式、将来的工作的争辩。这是一场为了认识现今的使命以及人性的定位和使命的争战。”[109]
在更早的还是在1938年的几次查经领会题为《工作的再思》一书中,他就“工作”,即相当于今日中国教会通用的“宣教”或“福传”,来界定使徒的宣教职分与“地方教会”弟兄们的关系,他就开始原创性地部署在中国各地如何建立使徒传统的教会模式。这就是说,防止出现教会内部的分党,或被世俗有权有势的教会远距离操控或支配,滑向大教会模式,他开始通过分析使徒的“工作”与地方教会特有的自治做出具体的设计,[110]其中有几段在这里需要我们来仔细琢磨和领会:
“我们必须记得使徒与教会的关系。使徒的职事乃是为着传福音,设立教会的。虽然圣经也说,神在(普遍的)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有使徒;但是,使徒的职事(不是个人)实在是与(地方的)教会完全不同的,完全二条路线的。乃是先有十二使徒,然后才有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设立。乃是先有保罗巴拿巴二使徒,然后才有各地教会的兴起。所以,使徒的工作,乃是完全在教会之先的。乃是先有使徒,后有地方教会。所以,使徒的工作定规不属于地方教会里的。”[111]
这些评述是倪柝声就使徒行传的教会职分做出思考所得。我们简要的引述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他关于启示录七个教会预言的思考不是在做书斋学问,而是进入历史和现实的事工需要。
究竟如何在当时的中国,军阀混乱,抗战救亡,世界大战,差会争雄等等现实中建立起使徒传统的教会,必定涉及到许多事工的权柄和责任。倪柝声对圣经的敬畏之心使得他完全回到新约教会传统中去获得启示。
“我们已经看见教会乃是地方的,是丝毫不受地方之外的干涉的,她也丝毫不干涉到地方之外。里面的事乃是由当地比较属灵的信徒,被立为长老来负责监督的。使徒乃是一个地方教会所没有的一个职分。至于各地传福音的工作,乃是神特别差遣使徒去作的。在没有教会的地方,使徒已经先有了,乃是他们来传福音,来设立教会。在已有教会的地方,虽然使徒可来作坚固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地方教会的组织中,却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使徒的工作与地方的教会,乃是完全不同的二种组织。教会的范围,只限于一地;工作的范围,是不限于一地的。限于一地的是教会,不限于一地的是工作。地方教会,对于工作,并不负任何正式的责任,虽然他们有属灵的责任。地方教会,如果愿意乐意帮助工作,就那个原因并非正式的,乃是乐意的。……使徒不能直接干涉地方的事。使徒只能提醒,提倡,劝勉而已。因为地方教会的正式责任乃是在长老身上。使徒所有的,不过是属灵的责任而已。教会如果灵性好,就要接受使徒的劝勉;他们如果灵性不好,就要不接受。在灵性上固然是大错了,但在正式上他们是有权柄可以自主的。教会对于工作,没有正式的关系,只有灵性上的关系。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就是教会要自立、自养、自传。这个问题的发生,就是因工作和教会混在一起,没有分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差会和教会混在一起。是差会替他们预备会所,是差会在那里替他们设立祷告会,是差会在那里替他们设立查经班,是差会在那里替他们预备礼拜堂作礼拜。结果到后来要他们自立,自养,自传就难了。如果一起头作工,就照着圣经作去,根本就不发生这些难题了。” [112]
这些言说已经涉及到使徒教会在中国重建(恢复)的过程中,如何在功效上建立制度和规范,即,教制议题了。其中倪柝声提到他那个时期,自立、自养、自传,即最初的“三自原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言说。这个非常关键,值得我们进一步专门去探讨。究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是如何从使徒传统获得亮光?同样,持守使徒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路德和加尔文,都是持守使徒传统,并在大公教会基本教理方面以古公教父传统为本,那么,在弟兄会传统和大公教会传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隐秘的联系呢?
我们需要另外专门的研究来探讨倪柝声神学思想中关于这个组织体制议题的种种设想和现实创制。可以说,对赵紫宸、丁光训、倪柝声三种不同类型的教会先贤的文本研究,必须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责任负担联系起来,我们在可以还原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才能够明白他们最初的想法和所遇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
第三,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政教关系在倪柝声神学系统的教会论中深层次包含的原则是什么?
为什么快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地方教会”,在本质上确确实实地在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既不依靠西方传教组织,无论是教义、教规、经济,还是政治、社会、伦理,也不以各种方式从国家那里获得财政支持和补贴,这就是说,使徒教会的模式,才是真正的“三自原则”,而同时,勤奋劳动,依法纳税,敬业守道,这不正是国泰民安情景下的使徒们的见证吗?无论是赵紫宸,还是丁光训,他们与倪柝声一样,都是这个民族基督徒中的蒙福者,尽管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完全各异,但是,他们的言说所发生的影响一直存在着。我们从他们各自的关于中国教会的异象中,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一样的,即,建立中国的教会,蒙神悦纳和赐福!
就倪柝声而言,今天,在世界基督教版图上,他所创建的中国弟兄会教会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就如同他所言的,起初的愿望是“弟兄相爱”的“弟兄们的运动”,后来,在严峻复杂的历史变迁和风云中,这个“可爱的小群教会”,开始演变成“中国土著教会”(李常受语),真正成为了在历史神学视野中的“弟兄会”教会。一种传统一旦建立,其必定会显现于各种言辞、规则、模型、范式中。我们研究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三位神学思想家时,应该看到他们既继承了不同的传统,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特定的传统。
法学思想家伯尔曼关于传统的一段评述在这里有一定的启迪,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他写道:“传统不仅仅是历史的连续性。一种传统是有意识和无意识因素的一种混合。用奥克塔威 ∙ 帕斯的话讲:‘传统是一种社会的可以看得见的一面——制度、遗迹、作品和物,但它尤其是社会的被淹没了的看不见的一面:信仰、希望、恐惧、压抑和梦想。’ ‘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113]
因此,目前已经显示出一种迫切性,即,把华人教会的不同传统进行有系统的比较,就各自渊源、传承和拓展等在历史变迁中的展示轨迹做出界定,以便帮助我们去理解各自不同对圣灵引领的不同侧面是如何领会并在工具论层面加以实施的。发生在个别“三自组织”领导层面和华人福音派个别有影响的领军人物与倪柝声传统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摩擦、误解和冲突,具有非常复杂的政治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若可以排除极端恶劣的唯利是图之政治动机,欺骗国家政权打击异己这一类政治权谋型诽谤言说不论,单单先就华人独立教会系统中以改革宗旗号来贬低中国地方教会来看,就非常有必要就不同的教会传统做系统的理性的研究。
这样,政教关系在自治、自养、自传层面来看,恰恰是研究赵紫宸、倪柝声、丁光训在各自不同时期所传承的不同教会传统中的极为有价值的议题。因为赵紫宸所遵循的自由主义神学、新正统主义神学和中华圣公宗传统,使得他对其所在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应该选择怎样的教会之路所做出的丰富思考中,政教关系就是一个极为有历史价值的着眼点。而丁光训在唯一合法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组织”中,依然保持着中华圣公宗传统中的教义、礼仪和政教关系基本原则。许多历史的细节可以让后人研究时思考他的言行举止后面所持守的神学理念和传统。而倪柝声在1950年以前留下的大量的文字足够后人去研究和寻找他的视野和思想中的政教关系之基本理念,也可以通过他作为中国弟兄会教会传统创建人的一系列行为来让后人就其基本理念做出廓清和解释。
第四,关于使徒传统与基督信仰之中国处境化
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议题必定要涉及赵紫宸、倪柝声和丁光训都先后经历的中国20世纪震荡时期的各种思潮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感受的。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和本色化运动。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简要地进入这个议题是为下一步的研究做铺垫,因为理解倪柝声的教会论,离不开把他那个时代的赵紫宸、丁光训之神学言说作为理解背景,同样,研究赵紫宸和丁光训不同处境中的神学思想之教会论,也可以把倪柝声的神学思想作为参照物,或者至少是理解域,以便让我们可以建立符合神学解释学原理的理解结构,以便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清晰的图景。
史学界研究这个背景的学者中,金陵神学院校友王治心可视为那个时代最有学术诚信的教会史学家之一。他确认1919年一战结束,在巴黎和会的背景下,非基同盟与本色运动,具有反帝仇外的民族主义民粹式激情。“(1922年的)非基同盟,不可谓非新思潮运动中的一种结果。我们看同盟反基的理由,大都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 [114]
在这个背景中,开始了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何为本色教会?解释的人很多,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自立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这个运动,是从‘基督教协进会’提倡起来的。诚静怡氏曾经说: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见《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协进会对教会之贡献》)。”[115]
“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全国大会’里所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第二段,举出九条关于‘本色教会’的意见,其间第三第六第七条说:
三,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是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这是我们教会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七,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116]
这些言语中的一些特定的术语非常有益于我们理解倪柝声所言的“很时髦的说法”这一时代主题。“中华基督教”这个概念,在王治心引用中的论述,今天来看,依然令人感动和敬佩!尽管充满着激情和美梦,但确实实实在在地引起了具有历史眼光和特定蒙召者的行动,赵紫宸、倪柝声、丁光训,他们先后在三个完全相异的教会处境和传统中,都在思考着“教会”之路。此外,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所留下的许多言论奠定了后来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制定的背景,也是将来我们需要给予重视和研究的。[117]而蔡元培等公共学者和思想家,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学术参照,他们对于非基运动、帝国主义和传教运动等的基本看法和见识,其实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去还原赵紫宸和倪柝声在1949年之前的公共知识氛围,因为赵紫宸、倪柝声在那个时代,一定是与各类学者一样,构成了完整的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思想者群体。
今天的中国,就其在世界历史景观上的现实形象和实际地位来说,可谓1840年代以来,民族自尊心和自强性得到恢复和重建最具说服力的时期。但是,就中国悠远的文明史而言,儒家传统中的忧患意识和天下为公之传统,反而不断地提醒有真正责任感的爱国人士,保持清醒的反省和自律意识,同时,对于像赵紫宸、倪柝声、丁光训这样具有熟悉历史教会伟大传统,同时,以圣经为信仰本体的神学思想家而言,十字架真理是超越性的永恒真理,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三一信仰如何以道成肉身的奥秘引导我们去爱邻舍、爱祖国、爱人类,最后荣耀归于三一上主,就一直是不可改变的生命之源和使命之在。
这就是我们要进入倪柝声的文本去明白和领会他的原初愿望的意义与价值。在整个中国基督教史上,他从非信经传统的教会观视野中去孜孜以求且真诚而敬虔地回到新约时期的初期教会中去建立中国本土教会,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和思考其特定作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他自己对使徒传统的如此向往,也可以在半殖民地、军阀混战、救亡图存的近代史大背景中凸显出内心深处的醒悟、蒙召和使命。
Carl Schmitt 写道:“基督教神学家属于教会所规定的一个等级(Stand),既非先知,也非作家。‘犹太人和异教徒中没有神学;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教,而且前提是,它所言说的是上帝的已成血肉之言(fleischgewordene Wort)。犹太人爱好解经(Exegesis), 异教徒搞神话学和形而上学;只有在言说了上帝成人之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学。’(佩特森) 使徒和殉道者同样不是神学家,他们宣道、见证;相反,神学则以具体论证的形式贯彻道之启示(Logos-Offenbarung)的延伸。神学仅仅存在于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之间。”[118]
因此,围绕着倪柝声的许多研究忽略了他并非大学教授做纯粹书斋式文本研究的神学家,一如路德、加尔文、卫斯理等教会历史人物,他是一位教会牧者,更是一位引领当时的弟兄们回归使徒教会的领袖人物,一位源自新约使徒教会传统的弟兄会教会在中国的承传者和创建者。我们对他的理解可以多个不同的视野,但不可以近代以来激进和极端宗派主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去强加一些标签或曲解于他及其所创建的本土传统。这就是我对其回归(用他特定的术语就是恢复)使徒教会信仰传统的粗浅而不全面的理解与解读。(全文完。)
2019年12月2日 星期一 东京
来源: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注释:
[103] 倪:1945.102。
[104] 倪:1945.106。
[105] 倪:1945.113。
[106] Richard J. Bauckham, 《启示录神学》(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邓绍光 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00,第8页。
[107]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来临中的上帝: 基督教的终末论》(Das Kommen Gottes, Christliches Eschatologie), 曾念粤 译,香港:道风书社,2002年,第184页。
[108] 莫尔特曼就此作出这样的评述:“‘宗教史私人事务’,现代社会以此为口号摆脱了各种基督教教派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但是这个运动本身又同时具有新的宗教职能。此时,宗教变成了私人崇拜(cultus privatus)。宗教现在被理解为精神和情感的事情。‘人格’之殊质 …..宗教与信仰必须关注孤独无定的灵魂,关注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一个因受现代社会纷扰而难以存在的世界……上帝乃是世界以及世界进程中的人类社会之源头与归宿,这一点已不再能够证明,然而,上帝是存在的超验基础,是个人依良心行事之能力的超验基础,这却是能够被证明的。要在此世之知识与活动的范围内为上帝造一安身之所已不复可能。这就使基督教向世界所宣讲的无非就是此一世界想要与闻的东西。” Jürgen Moltmann,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the Future, pp.. 113, 117. 转引自:伯尔曼(Harold J. Berman), 《法律与宗教》(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 梁治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3页。
[109] 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 《盼望神学》(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u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schen Eschatologie), 曾念粤 译,香港:道风书社出版,2007年,第186页。
[110] 林荣洪就此的评价为:“倪氏是‘地方教会’的领导人,《工作的再思》是这个教会运动的神学基础。今节录该书中〈工作与教会〉一篇,可说明倪氏的教会观,有别于传统的一般观念。他认为教会是地方性的,‘工作’是超地方的。这个分别于‘一地一会’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林荣洪 编:《近代华人神学文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86年,第320页。
[111] 倪柝声:《工作的再思》,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30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79年再版,第198页。
[112] 倪柝声:《工作的再思》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30册,台北:台湾福音书房,1979年再版,第222-242页。
[113] 伯尔曼(Harold J. Berman): 《法律与革命》(Law and Revolution)(第一卷),贺卫方 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729页。
[11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40年初版,2007重印,第205页。
[115] 同上,第213页。
[116] 同上,第214页。
[117] 关于无神论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参考文献为:李大钊 著《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蔡和森 著 《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独秀 著,《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8年;陈独秀 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恽代英 著《恽代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8] 施密特(Carl Schmitt): 《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刘小枫 编,刘宗坤 吴增定 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