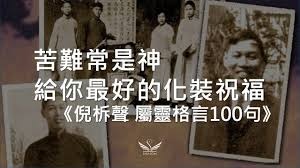基督的七步降卑在解经历史上的重要观点
引言
“基督的七步降卑”是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它描绘了道成肉身的圣子为完成人类救赎所经历的深刻谦卑过程。这一概念主要根植于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5-8中的赞美诗,该段经文构成了理解基督“虚己”(κένωσις, kenosis)及其顺服至死的基础 。在基督论中,“降卑”(ταπείνωσις, tapeinosis)一词特指上帝之子自愿舍弃其神性荣耀,取了人性,并为人类的救赎而承受苦难的各个阶段 。
基督教神学传统上将基督的生命分为“降卑状态”和“高升状态”。降卑状态涵盖了祂的尘世生命、受苦和死亡,而高升状态则包括祂的复活、升天以及坐在上帝右边 。这一框架突显了基督救赎工作的整体轨迹。
本报告旨在对“基督的七步降卑”这一教义进行全面的历史和神学分析,探讨基督教思想史上不同时期和重要神学运动如何解释和发展这一教义。报告将深入研究相关的解经辩论、神学意涵,以及基督虚己的持久意义。
第一章:圣经中的降卑:腓立比书2:5-8的解读
“虚己”(Kenosis)的含义与争议
“虚己”(κένωσις, kenosis)一词源自希腊动词 kenoō,意为“倒空”或“使自己一无所有”,在腓立比书2:7中用于描述基督的行动 。这一概念是理解基督道成肉身和降卑本质的关键。
关于“虚己”的具体含义,神学界存在着重要的争议。19世纪的虚己论基督论中,一些解释认为圣子在道成肉身期间暂时放弃或剥夺了某些神性属性,例如全知、全能 。然而,正统神学普遍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上帝不可能停止是上帝,或失去其本质属性 。相反,更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基督是“遮蔽”或“自愿不使用”其神性特权和荣耀 。这意味着祂并未停止完全是上帝,而是选择在人性限制下运作 。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如果基督真的剥夺了其神性属性,那将损害祂在尘世事奉期间的完全神性,从而引发关于祂能否完美地代表上帝并完成救赎的疑问。如果这是一种遮蔽,则既保留了祂的完全神性,又肯定了祂人性经验和受苦的真实性,这对于祂作为救主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场辩论突显了在不损害基督神人二性任何一方的情况下,阐明其悖论的持续挑战。
七步降卑的具体阶段
虽然圣经并未明确列出“七步”,但各种神学传统根据腓立比书2:5-8及其他新约经文,将基督的降卑分为不同的阶段。一种常见的划分,尤其是在某些新教传统中,包括以下七个阶段:
* 倒空自己(Self-emptying / Emptying Himself):基督虽有神的形像,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这指的是祂自愿放下神性特权和荣耀的行动 。
* 取了奴仆的形狀(Taking the Form of a Servant):祂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而非坚持自己作为主的权利 。这强调了祂降卑到卑微的地位 。
* 成为人的样式(Being Born in Human Likeness / Becoming in the Likeness of Men):祂真正成为人,有血有肉,承受人的软弱,但无罪 。这包括祂的神奇受孕和卑微降生 。
* 降卑自己(Humbled Himself):祂不仅成为人,更在祂的整个生命中主动降卑自己 。这包括经历尘世的苦难,如被拒绝、受试探和被藐视 。
* 成为顺从的(Becoming Obedient):祂凡事顺从父神的旨意,完美地遵守了律法 。这种顺服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即顺服律法的要求和惩罚 。
* 顺从至死(Obedi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祂的顺服延伸到最终的牺牲,甘愿面对死亡 。
* 且死在十字架上(Even Death on a Cross):祂降卑的顶点是死在羞辱和被咒诅的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承担了上帝的愤怒 。这是虚己的终极行动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传统也将“埋葬”和“降到阴间”视为降卑状态的一部分 。
其他圣经文本对基督降卑的补充
除了腓立比书2:5-8,其他圣经文本也补充了对基督降卑的理解。以赛亚书53:3预言了基督的降卑,指出“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希伯来书2:9-10则论及耶稣“比天使小一点”,并“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 。路加福音14:11中“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的教导,也被用来连接基督的谦卑与更广泛的属灵原则 。
表1:基督七步降卑的圣经定义与主要阶段
| 阶段 | 描述 | 圣经依据 | 神学意义 |
|—|—|—|—|
| 1. 倒空自己 | 基督虽有神的形像,却自愿放下其神性特权和荣耀。 | 腓立比书2:6-7a | 彰显基督自愿的谦卑与舍己之爱。 |
| 2. 取了奴仆的形像 | 祂取了奴仆的形像,而非坚持自己作为主的权利。 | 腓立比书2:7b | 强调祂降卑到卑微的地位,与人类认同。 |
| 3. 成为人的样式 | 祂真正成为人,有血有肉,承受人的软弱,但无罪。 | 腓立比书2:7c;路加福音2:7;马太福音2:13-22 | 肯定基督完全的人性,为救赎奠定基础。 |
| 4. 降卑自己 | 祂在整个生命中主动降卑,经历尘世的苦难和藐视。 | 腓立比书2:8a;以赛亚书53:3;路加福音4:29 | 展现基督在人类境况中的真实受苦与顺服。 |
| 5. 成为顺从的 | 祂凡事顺从父神的旨意,完美地遵守了律法。 | 腓立比书2:8b;希伯来书2:9-10 | 强调基督的完全顺服,成就了律法的义。 |
| 6. 顺从至死 | 祂的顺服延伸到最终的牺牲,甘愿面对死亡。 | 腓立比书2:8c | 凸显基督顺服的彻底性,直至生命终结。 |
| 7. 且死在十字架上 | 祂降卑的顶点是死在羞辱和被咒诅的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承担上帝的愤怒。 | 腓立比书2:8d;加拉太书3:13 | 基督救赎工作的核心,承担罪的咒诅与上帝的愤怒。 |
第二章:早期教父时期:救赎论的奠基
亚他那修:道成肉身与战胜死亡
亚他那修(约公元296-373年)强调道成肉身是基督降卑的核心行动,对人类的救赎至关重要 。他认为,圣子成为人是为了消除人类的败坏,因为人类因悖逆而陷入死亡的权势之下 。
亚他那修的核心论点是,人类无力对抗死亡和败坏,因此需要上帝亲自介入。永恒的圣子成为拿撒勒的耶稣,献上自己的死亡作为牺牲,以彻底摧毁死亡本身 。亚他那修对赎罪的看法主要是本体论的,侧重于人性的再创造,而非仅仅是法律上债务的取消。基督的死亡被视为“死亡的死亡” 。
亚他那修对道成肉身和基督之死作为本体论解决方案的强调,与后来更侧重法律层面的赎罪理论形成了对比。他认为败坏是“附着在身体上”的,因此“生命需要与身体交织在一起”才能摆脱败坏 。这意味着基督的降卑不仅仅是为了人类付出代价,更是通过上帝亲自取了人性并经历死亡,从内部“改变”人性。这种观点为理解降卑是一种深刻的神性团结和再创造行为奠定了基础。这种对本体论转化的早期强调(从φθόρα到ἀφθαρσία,即从败坏到不朽)是东方正教神学中“神化”(theosis)概念的基石 ,即人类通过恩典、通过变得圣洁来参与上帝的救赎工作 。
奥古斯丁:谦卑作为罪的解药与救赎的途径
希波的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对西方基督徒理解基督的谦卑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奥古斯丁而言,谦卑不仅是一种道德美德,更是基督救赎工作的核心方面,是人类骄傲的解药 。
他论证说,基督的谦卑既具有救赎性,又具有榜样性。基督甘愿降卑为人,并死于残酷的十字架上,从而医治了骄傲的“疾病” 。奥古斯丁经常使用医学意象,称基督为 medicus humilis(谦卑的医生),祂医治了骄傲的顽疾 。
奥古斯丁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基督的谦卑直接与救赎论联系起来,将其视为与上帝和解的“核心手段” 。这超越了简单地陈述基督是谦卑的,而是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即骄傲是“根本的罪”,而基督的谦卑则是“特定的解药” 。这意味着效法基督的谦卑不仅是道德上的追求,更是基督徒生命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源于基督的救赎工作。奥古斯丁对谦卑作为骄傲解药的强调,为西方神学思想,包括后来的罪、恩典和基督教伦理概念,树立了强大的先例。它突显了基督降卑对信徒个人品格的“转化力量”,超越了对救赎纯粹外部或法律的理解。这与后来虔敬主义对个人转化和效法基督的强调相契合 。
第三章:中世纪经院哲学:赎罪论的系统化发展
安瑟伦的满足论:荣誉与亏欠的视角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约公元1033/4-1109年)在其著作《为何是神人》(Cur Deus Homo)中发展了满足论(Satisfaction Theory of Atonement),该理论在西方神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
安瑟伦摒弃了早期的“赎金论”(即向撒旦支付赎金的观点),转而从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罪恶所造成的“无限亏欠”的角度来阐释赎罪 。他认为,罪恶侮辱了上帝的荣耀,需要无限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只有神人才能提供。基督,即使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也完美地尊荣了上帝,偿还了无法偿还的亏欠 。
安瑟伦的理论代表了赎罪神学的一个重要“范式转变”,从宇宙性的争战(赎金论)转向以神圣公义和荣誉为中心的“法律框架” 。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人类的罪恶对无限尊贵的上帝造成了“无限的亏欠”,这“必然要求”无限的偿付。这直接导致了“只有神人”才能提供这种满足的结论,因为只有上帝拥有无限的功德,而只有人类负有债务 。因此,基督的降卑,最终体现在祂的死亡,不仅是爱的行动,更是恢复上帝荣誉的“必要法律交易”。这一理论深刻地塑造了西方对基督降卑的理解,强调了其“客观性”和“替代性”。它为后来的刑罚替代赎罪理论奠定了基础 ,即基督为人类的罪承担了刑罚。它也突显了一个张力:虽然基督的降卑在某种意义上对上帝而言是“不合宜的”,但对救赎而言却是“最合宜的” 。
托马斯·阿奎那:基督双重人性的受苦与救赎
托马斯·阿奎那(约公元1225-1274年)在其巨著《神学大全》中整合并完善了包括安瑟伦满足论在内的早期神学思想 。
阿奎那肯定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并认为道成肉身对于恢复人类脱离原罪的本性是必要的 。他论证说,基督的受苦和死亡,是出于“超凡的爱和顺服”,为人类的罪提供了“超额的赎罪” 。
阿奎那在安瑟伦的满足论基础上增添了重要的细微之处。他认为,基督的受苦,虽然在“质料”上是一种“刑罚”,但其“形式”却是“爱”(charity) 。这意味着受难的救赎意义并未被简化为仅仅是法律要求或一位喜悦受苦的愤怒上帝 。相反,上帝“愿意基督受苦,作为医治和提升罪人的恰当方式” 。这为满足论引入了更具“目的论”和“道德”的维度,强调了基督自愿的、充满爱的顺服,而非仅仅是冷冰冰的法律交易。阿奎那的综合为理解基督在天主教神学中的降卑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他强调基督的受苦是出于爱和顺服的行为,而非仅仅是法律上的偿付,这使得对赎罪中神圣之爱的理解更为丰富。这也与后来批评满足论过于法律化或惩罚性的观点形成对比 。
中世纪对基督谦卑形象的强调
13世纪,尤其是在方济各会的影响下,对“温柔的耶稣形象”及其从诞生到死亡的谦卑的强调,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种形象通过圣诞场景和虔敬实践得到推广 。
这一时期,平信徒对宗教虔诚的参与也显著增加,他们专注于默想基督的生平与受苦,并寻求“效法基督” 。这包括通过自我鞭打等行为来感受与基督受苦的亲近 。
中世纪的这一转变,尤其是方济各会的影响 ,代表了一种向更具“情感性和个人性地参与”基督降卑的“趋势”。这是对可能过于抽象的经院神学的“回应”,旨在使基督的受苦更具共鸣,并对普通信徒产生情感上的影响 。圣诞场景的推广 和“效法基督”文学的强调 是促进这种个人虔诚的“因果因素”。这一发展预示了后来的虔敬主义运动 ,通过强调基督受苦的主观经验和道德榜样。然而,它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即将基督的工作简化为纯粹的道德模仿,而非独特的救赎行动,这种张力在后来的神学辩论中变得更加明显 。
第四章:宗教改革时期:十字架神学与谦卑的再诠释
马丁·路德:苦难中的上帝启示与谦卑神学
马丁·路德(公元1483-1546年)发展了他的“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这与他所称的“荣耀神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路德而言,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并非来自荣耀、能力或人类理性,而是来自上帝在十字架上的隐藏、软弱和受苦 。十字架同时启示了上帝的怜悯和愤怒 。他强调上帝使骄傲的降卑,使谦卑的升高,并且受苦是成为真正神学家的道路 。
路德还区分了将基督作为“礼物”来接受(因信称义)和将祂作为“榜样”来效法以服侍邻舍 。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是神学方法论上的一次根本性“重新定位”。它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即苦难不仅是罪的后果,更是“上帝启示的主要场所”。这与寻求通过理性和创造的荣耀来认识上帝的经院自然神学“相悖” 。这意味着基督的降卑,特别是十字架,是理解上帝的爱和公义的“唯一真实视角”,它挑战了人类的骄傲和自给自足。他将基督视为礼物和榜样的区分 是理解基督徒生活的“关键要点”:与基督的联合先于并促成效法,从而避免律法主义 。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成为新教基督论的基石,强调了基督降卑的深度及其对救赎的核心作用。它也为后来的虚己论辩论奠定了基础,突显了上帝在软弱中同在的悖论,尽管路德本人并未发展出完整的虚己论基督论 。
约翰·加尔文:降卑与高升的同步性
约翰·加尔文(公元1509-1564年)也广泛讨论了基督的降卑,通常与祂的高升并置。他强调基督的降卑是自愿的顺服行为 。
加尔文与严格的“先降卑后高升”的线性发展不同,他提出了一种“同步性”,即基督即使在降卑期间,其神性也仍是高升和荣耀的,尽管祂的荣耀被“隐藏且未发挥其力量” 。他认为,基督作为神人,其神性同时处于降卑状态,而其人性则处于高升状态 。
加尔文的“降卑中的高升”概念 是对虚己论辩论的一个精妙“细化”。它直接“回答了”基督如何在承受人性限制的同时仍是完全上帝的问题。他的观点意味着基督的神性属性是“被遮蔽或未被使用”,而非被放弃 。这与那些认为神性属性暂时丧失的更激进的虚己论观点“相矛盾” 。其“含义”是,基督的降卑是一种主权的、主动的选择,而非被动的减损,从而维护了祂神性本质的完整性。加尔文的解释在归正宗神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提供了一个在基督降卑的整个过程中,既肯定其完全神性又肯定其真实人性的框架。这种理解也塑造了归正宗对基督神人二性之间“属性相通”(communicatio idiomatum)的看法 。
改革宗神学对降卑阶段的界定
改革宗神学,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所规范的,通常将基督的降卑状态分为五个阶段:道成肉身、受苦、死亡、埋葬和降到阴间 。
* 道成肉身:基督卑微降生,服在律法之下,承受人性的软弱,其荣耀部分被遮蔽 。
* 受苦:经历尘世的苦难,包括被拒绝、受试探、身体疼痛和灵魂的痛苦 。
* 死亡:死在被咒诅的十字架上,承担上帝的愤怒和人类的罪恶 。
* 埋葬:被安放在坟墓中,象征着祂死亡的真实性和完成 。
* 降到阴间:改革宗神学将其解释为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处于死亡的权势之下,或经历上帝愤怒的完全真实性,而非文字意义上的阴间之旅 。
改革宗传统对降卑阶段的精确列举 代表了对圣经教导的“系统化编纂”,旨在实现清晰和全面的覆盖。这一框架通常将每个阶段与基督的“替代性工作” 建立“因果关联”,即祂代替人类履行律法并承担其刑罚。对“降到阴间”的解释为承受上帝的愤怒 ,而非字面意义上的旅程(尽管某些传统有所不同 ),是强调其受苦属灵深度的“关键区别”。这种结构化的方法为理解基督在归正宗新教中的降卑范围和效力提供了坚实的神学基础,巩固了刑罚替代赎罪论的核心地位 。它也突显了基督顺服在祂降卑所有阶段中的持续性。
第五章:近代与当代神学:虚己论的持续探讨
17-19世纪虚己论争议:神性属性的舍弃或隐藏
17世纪,路德宗神学内部爆发了“虚己-隐藏论争议”(Kenosis-Krypsis Controversy),主要发生在图宾根和吉森两地的神学院之间 。吉森学派(虚己论)认为,基督在降卑中“剥夺”或“暂时停止使用”了某些神性属性(如全能、全知、无所不在),以过上真正的人类生活 。图宾根学派(隐藏论)则坚持基督“保留”了所有神性属性,但在其人性状态中“隐藏”或“并非总是使用”它们 。这是一种神性属性的“秘密”(krypsis)运用 。
19世纪,德国虚己论者如G. Thomassius、F.H.R. von Frank和W.F. Gess提出了更激进的理论,认为道(Logos)“限制了自身”或“剥夺了耶稣的神性属性” 。英国虚己论者(如H.R. Mackintosh、P.T. Forsyth)则侧重于“恩典性的降尊”和耶稣“有限的人类意识”的真实性,这往往是对圣经批判的回应 。
17-19世纪的虚己论辩论是宗教改革强调基督真实人性的直接“结果”,也是在“属性相通”(communicatio idiomatum)背景下,持续尝试调和基督完全神性与真实人性的体现 。吉森-图宾根争议 展现了在维护神圣无感性与肯定基督真实受苦和限制之间的“张力”。19世纪“圣经批判学”的兴起 进一步“促使神学家”以一种不否定其神性的方式解释耶稣明显的人性限制(例如,不知道审判日的时间 )。这种智识/历史压力与教义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一个关键主题。这些辩论,尽管复杂,但突显了基督论的持久挑战:如何在不混淆或分离的情况下肯定基督的两种本性。各种虚己论理论,尽管有些被视为异端 ,但它们促使神学家更深入地思考道成肉身的“机制”及其对神性属性的含义,为当代关于神圣无感性与自我限制的讨论铺平了道路。
敬虔主义:个人经验与基督受苦的效法
敬虔主义于17世纪末兴起,强调个人虔诚、属灵重生和圣洁的基督徒生活 。它通常将“主观经验”作为属灵确信的基础 。
虔敬主义者常将十字架视为核心,但他们通过“主观经验”和与基督受苦的“个人认同”来理解基督的受苦,而非仅仅是客观称义 。这导致了对“效法基督的受苦”和“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的强调 。
虔敬主义对“个人经验”和与基督受苦的“情感团结”的强调 是对正统新教中教义枯燥和知识主义的“回应” 。虽然它培养了深刻的虔诚和对实际圣洁的渴望 ,但也引入了“潜在的风险”:将救赎简化为“主观经验”或人类努力 。路德关于在将基督作为榜样“之前”先将祂作为礼物来接受的警告 突显了这与基于恩典的神学之间的“矛盾”。虔敬主义对基督榜样和受苦的强调影响了后来的福音派运动,并持续塑造着大众虔诚。然而,它倾向于将主观感受置于客观真理之上,可能导致“律法与福音的混淆” ,使救赎的确信与个人感受或行为而非基督已完成的工作挂钩。
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神学:基督作为道德榜样
启蒙运动对理性和历史批判的强调导致了对耶稣的重新解释,通常淡化了超自然元素,而将基督视为“道德教师”或“榜样” 。受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和阿尔布雷希特·里奇尔等人物影响的自由主义神学,常将基督的死视为上帝之爱的“彰显”(道德影响论)而非刑罚替代 。自然神论,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普遍拒绝基督的神性及其神迹,将其视为一位拥有道德准则的尊贵之人或先知 。
启蒙运动 作为一种“因果力量”,推动了基督教教义“理性化”的“趋势”。这“导致”了自由主义神学对基督降卑的重新解释,通常将其角色从一位施行客观赎罪的神圣救主,“简化”为主要的“道德榜样” 。这与传统的替代性赎罪观 和基督神性对救赎的必要性 “相矛盾”。其“含义”是从“基督做了什么”(客观赎罪)转向“基督教导/启发了什么”(主观道德影响)。这一时期表明,哲学转变(理性主义)如何深刻地“影响”神学解释,导致对超自然和基督降卑独特救赎本质的淡化。它也突显了历史批判学与教义宣示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 。
当代神学:苦难神学与虚己论的新视角
当代神学继续探讨基督的降卑,常与现代的苦难经验进行对话。尤尔根·莫尔特曼的“十字架神学”和“盼望神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主张一种“三一虚己论”,认为上帝真正参与了苦难 。莫尔特曼认为,十字架揭示了“三一关系内部的苦难”,挑战了神圣无感性的古典观念 。
当代虚己论基督论探讨基督统一的意识,通常强调祂自愿“暂停”神性荣耀(krypsis)而非剥夺属性 。莫尔特曼的工作 是对邪恶和苦难问题的“当代回应”,旨在使上帝在苦难中的同在更易于理解。他引入了对虚己论的“激进重新诠释”,将其扩展到“内在三一” ,这意味着上帝并非“超然于”时间或痛苦。这“挑战了”神圣无感性的传统教义,暗示上帝“真正参与”了苦难。其“含义”是对上帝在人类痛苦中团结的更深理解,提供了一个更具同情心的上帝形象 。当代神学的这一趋势旨在弥合抽象教义与生活经验之间的鸿沟,重新强调基督降卑对于理解和应对当今人类苦难的“相关性”。它代表了虚己论思想的持续“演进”,超越了早期关于神性属性的辩论,转而探索上帝自我舍己之爱的“关系性和同情性”维度。
结论
基督七步降卑的教义,根植于腓立比书2:5-8,在基督教历史中是一个动态且不断演变的概念。从早期教会对本体论转化(亚他那修)和谦卑作为骄傲解药(奥古斯丁)的关注,到中世纪对法律满足(安瑟伦)和慈善顺服(阿奎那)的强调,再到宗教改革时期对十字架作为上帝在软弱中启示(路德)以及降卑与高升同步性(加尔文)的重新定位,每个时期都贡献了独特的见解。
近代和当代神学继续深化对“虚己”的理解,辩论基督“倒空”的性质,并探讨其对神圣无感性以及上帝与人类苦难团结的意义。在这些历史观点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张力是如何在维护基督完全神性与肯定祂人性受苦和限制的真实性与深度之间取得平衡。
基督七步降卑的教义对当代信仰和实践具有深远意义。它仍然是基督教救赎的基石,彰显了上帝在处理罪恶和死亡方面的无限之爱和公义。它为信徒提供了深刻的伦理榜样,呼召他们虚己、顺服和服侍他人 。当代解释突显了上帝在人类苦难中的同情性同在,在痛苦时期提供了盼望和意义。这一教义也持续引发对神人奥秘的深刻神学反思,挑战了对神圣能力和人类软弱的简化理解。
表2:历史时期主要神学家/运动对基督降卑的观点对比
| 历史时期 | 神学家/运动 | 核心观点 | 关键概念/术语 | 救赎论关联 |
|—|—|—|—|—|
| 早期教父时期 | 亚他那修 | 道成肉身是战胜死亡和败坏的本体论转化。 | 道成肉身,本体论救赎,死亡的死亡,神化(Theosis) | 基督取了人性以从内部再创造人类,摧毁死亡的权势。 |
| | 奥古斯丁 | 基督的谦卑是医治人类骄傲的解药,是救赎的核心途径。 | 谦卑,罪的解药,谦卑的医生(Medicus Humilis) | 基督的谦卑是与上帝和解的中心手段,转化个人品格。 |
| 中世纪经院哲学 | 安瑟伦 | 基督的降卑是为满足上帝的无限荣誉和偿还人类罪债的必要法律行动。 | 满足论,荣誉与亏欠,神人(God-Man) | 基督通过完美顺服和死亡,替人类偿还了罪债,恢复上帝的荣誉。 |
| | 托马斯·阿奎那 | 基督的受苦是出于爱和顺服的行动,其刑罚是手段,爱是其形式,旨在医治和提升罪人。 | 超额赎罪,爱(Charity)作为满足的形式,双重人性 | 基督的爱与顺服提供了超额赎罪,旨在医治和提升罪人,而非仅仅法律偿付。 |
| | 中世纪虔诚运动 | 强调对基督谦卑形象的情感投入和个人效法。 | 温柔的耶稣形象,效法基督 | 促进个人虔诚和道德转化,但存在将救赎简化为道德模仿的风险。 |
| 宗教改革时期 | 马丁·路德 | 上帝在基督的苦难和十字架中启示自己,挑战人类骄傲,强调因信称义。 | 十字架神学,苦难中的启示,基督为礼物与榜样 | 基督的苦难是上帝救赎之爱的核心启示,是信徒称义和效法的根基。 |
| | 约翰·加尔文 | 基督的神性在降卑中被遮蔽但未减损,其降卑与高升具有同步性。 | 降卑中的高升,荣耀的遮蔽,属性相通 | 基督的降卑是自愿的顺服,其完全神性在受苦中得以维护,为赎罪奠定基础。 |
| | 改革宗神学 | 系统地界定基督降卑的五个阶段,强调其替代性、顺服性及承担上帝愤怒。 | 道成肉身、受苦、死亡、埋葬、降到阴间,刑罚替代赎罪 | 基督在所有降卑阶段中替代性地履行律法并承担罪的刑罚,成就救赎。 |
| 近代与当代神学 | 17-19世纪虚己论争议 | 辩论基督在道成肉身中是否剥夺或隐藏了神性属性。 | 虚己(Kenosis),隐藏(Krypsis),神性属性的剥夺/隐藏 | 探讨道成肉身的机制,在肯定神人二性完整性中寻求平衡。 |
| | 敬虔主义 | 强调个人属灵经验和与基督受苦的个人认同与效法。 | 主观经验,个人效法,基督中心的生活 | 促进个人虔诚和圣洁生活,但可能导致将救赎系于主观感受或人类努力。 |
| | 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神学 | 将基督视为主要的道德榜样,其受苦是上帝之爱的彰显。 | 道德影响论,历史耶稣,理性主义 | 侧重基督的教导和榜样作用,淡化其客观赎罪的超自然性。 |
| | 当代神学(如莫尔特曼) | 探讨上帝在三一关系中真正参与苦难,挑战神圣无感性。 | 苦难神学,三一虚己论,神圣无感性 | 强调上帝在苦难中的团结和同情性同在,使信仰在苦难世界中更具相关性。 |